注:文章搬运自微信公众号“吃粥饭的碗”《鲁迅作品赏析》系列。鲁迅,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,新文化运动的旗帜,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,更是对人性、生存和人类困境的深刻反思。他捉笔为刀,解剖了中国,解剖了千年的历史,更解剖了每个人,让那些血淋淋的、赤裸裸的、人们不忍直视的东西展露出来。他以笔为枪直刺向笼罩着中国的,看似华美却黑暗幕布,让天空鬼闪眼,让月亮窘得发白。随着时间的侵蚀,鲁迅必将越来越模糊,模糊的是血肉,而非风骨,风骨嶙峋而坚硬,是任何时候都磨不平的,风骨傲立,血肉亦然不可风化,鲁迅先生二十二岁的热血,在三十七岁时凝聚,倾注在每一篇文章中,倾注在每一个被世间薄凉遗弃的灵魂里,一片一片皆是血肉,孔乙己是一片,祥林嫂是一片,华小栓是一片,阿Q也是一片,一片一片拼凑起来,才是鲁迅,他并非冰冷的雕像,刻板的老师,而是与你我一样,有血有肉的一个人,便是这样有血有肉的人,才构成中国这棵参天大树,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。时光荏苒,一百年过去了,一代又一代人逝去了,仿佛痛苦和磨难的历史也飘散了,现在很多人早已忘记那个时代,在昏暗苦守着希望,在死水中等待火焰,在牢笼中等待死亡,在死亡中等待新生。我也会引着大家的脚步,精选十篇文章,重新感知鲁迅先生,从飘摇的社会历史,感知颠沛的个人经历,从文本的拆解中,感知他的沉默,愤慨,迷惘,以及温热,感知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——每个尚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应去感知,而不应忘却。
正文:
好友兼著名报刊编辑孙伏园曾问过鲁迅,在短篇小说,最喜欢的是哪一篇,鲁迅先生回答说:《孔乙己》。相比于《药》的鲜血淋淋,《狂人日记》的满纸吃人,《阿Q正传》极具象征意义的“精神胜利法”,《孔乙己》就显得平淡了些,只是一个酸腐文人哀漠地死去罢了,可鲁迅为何偏偏对《孔乙己》偏爱有加呢?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篇看似平淡的《孔乙己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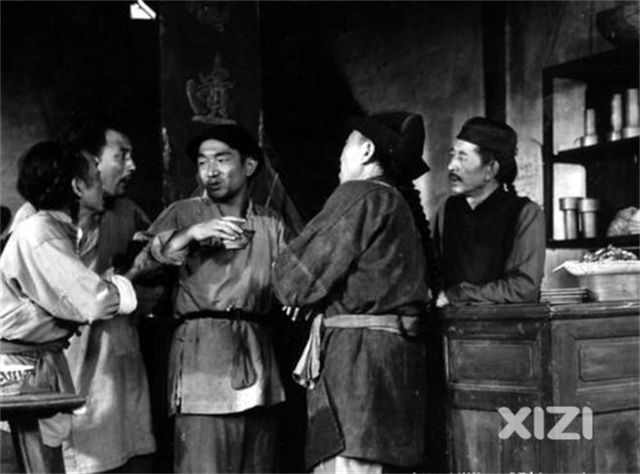 描述:1981年电视剧《孔乙己》剧照
描述:1981年电视剧《孔乙己》剧照
说起孔乙己,很多人耳熟能详,“读书人的事,能算偷么?”,“多乎哉?不多也。”文章的题目叫孔乙己,我们通常也把孔乙己当成主要分析对象,其实故事中的配角也很重要,比如丁举人、小伙计,掌柜,正是这些配角才构成了孔乙己所处的“社会环境”,所以小说一开始,并未交代孔乙己,而是这些配角和社会环境。
开头先写了酒店的格局,划分开短衣帮和长衫主顾,短衣帮多是出苦力干活的人,他们怎么喝酒呢——靠柜外站着,热热的喝了休息。而长衫主顾就不同了,鲁迅写道:只有穿长衫的,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,要酒要菜,慢慢地坐喝。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,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,柜里面预备着热水,可以随时温酒。做工的人,傍午傍晚散了工,每每花四文铜钱,买一碗酒,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,——靠柜外站着,热热的喝了休息;倘肯多花一文,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,或者茴香豆,做下酒物了,如果出到十几文,那就能买一样荤菜,但这些顾客,多是短衣帮,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只有穿长衫的,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,要酒要菜,慢慢地坐喝。
这一开头,看似是非常平淡的叙述,无形中划分开了鲁镇的社会阶层,文人士大夫阶层和底层劳动者。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做工的人,没有坐的地方,他们怎么休息呢?也许坐在门槛上或者地上,也许靠在墙上、柜台上,而酒店里明明是提供桌椅板凳的,为什么不进去坐呢?也没有任何规定说——穿短衣服的,不能进去坐,或者不点菜的不能进去坐,后面孔乙己还会买茴香豆当下酒菜,但他也不会到房间里去、舒舒服服地坐着喝酒吃菜。那么只可能有一种解释,下苦力的短衣帮认为自己不配坐进房间里喝酒。也许是因为消费少,影响别人做生意,更可能是天然地认为自己身份地位不配,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尊卑思想在作祟。细细想想,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合理,同样是消费者,为什么有的人只配站着,有的人却可以坐着?可退一步说,而且即便进去了,也会遭到长衫主顾的鄙夷的目光,这些短衣帮的佃农,每日辛苦劳作,忙忙碌碌,为什么不能被人尊重呢,就要比长衫低一等,只能靠在门口喝酒,而那些长衫人,又做出过什么贡献呢,兴许还不如短衣帮呢,无非家里土地多,或者有点功名,可他们穿着长衫,就高人一等,悠悠闲闲吃着小菜,喝着小酒——所有人却觉得天经地义,短衣帮根本不会去质疑,更不用反抗了。写完了这些,孔乙己还是未出现,鲁迅又用二百多个字交代了掌柜和小伙计,大概说小伙计笨笨傻傻的,不太会做事,伺候不好长衫主顾,也不会掺水糊弄不了短衣帮的人,掌柜对他没有好脸色,主顾们对他也没好气,只能安排他去温酒。这段话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,大家不妨试一试,把小伙计这段自述删掉,《孔乙己》这篇文章也是成立的,也是通顺的,甚至表达意义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,鲁迅先生又是以精练著称的作家,写这段做什么呢,小伙计的个人遭遇和《孔乙己》有什么关系呢?其实这段看似平静的叙述,蕴含的内容是很深的。我们先说掌柜,如果把鲁镇这个酒店看作小社会,这个小社会分成了读书的士大夫上等人和出苦力的下等人。掌柜恰好处在中间,他的态度就很有趣了,一面卑躬屈膝,努力地侍奉上等人,一面又在想办法欺负下等人。好多人说掌柜在酒里掺水这个行为是奸诈、狡猾的表现。而我认为,尽管鲁迅没有写明,掺水大概率针对短衣帮的,因为掌柜不敢这么对长衫主顾,从态度上说,掌柜唯恐小伙计伺候不好,二来孔乙己偷东西被打成残废,你一个小小的掌柜,敢糊弄各位“大人”,怕也是活腻了。我们再仔细回顾下鲁迅对短衣帮的买酒描写——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,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,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,然后放心,在这严重监督下,羼水也很为难。这说明了什么呢?短衣帮是知道老板常常掺水的,分明是个黑店,我们不妨再去想,倘若一名短衣佃农没有监督,真喝了掺水的酒,能怎么办呢?他们大概也不会去怪老板,只能怪自己不小心。这种行为看似是对掌柜掺水的反抗,实际是消极的,冷漠的,因为监督打酒的人,只愿意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,别人怎么样不在乎——短衣帮默认掺水的行为,只要不落在我头上就行了。这就是 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,搞不好别人喝到了掺水的酒,他还心里暗暗高兴呢。所以说这种行为是消极而冷漠的,消极是没有任何社会意义,无法改变社会现状;冷漠是对他人的冷漠,只关心自己的利益。这些描写都给社会环境定了一个“冷漠”的基调。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名言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他在呼吁,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人们皆与我有关,人们就是社会。人们越来越冷漠,社会现状就会越来越糟糕,所有苦难人的痛苦,本就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你看见别人遇到了一点不公正的事情,漠然置之,迟早有一天,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,不仅你自己,你的父母,你的孩子,都要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,也很可能遭遇同样的事情。
回过头来我们说文章,开头表述里面,短衣帮的态度就很有趣了,自己站着喝酒,对坐着喝酒的社会顶层没有半分的质疑,敢质疑的呢,是地位稍高一点的掌柜,但只是消极而冷漠的质疑,对于掺水几乎等同于纵容,没有任何反抗的想法。
鲁迅先生说:勇者愤怒,抽刃向更强者;怯者愤怒,却抽刃向更弱者。这句话也可以同样应用在掌柜身上,掌柜不敢对长衫主顾如何,抽刀向更弱者——往酒里掺水欺负短衣帮,对小伙计一脸的凶相,还天天调笑孔乙己;短衣帮不敢对长衫主顾和掌柜如何,抽刀向更弱者,对小伙计没好声气,也调笑孔乙己作乐。而小伙计就更有趣了,他是个十几岁的小孩,如果没有孔乙己,小伙计才是整个咸亨酒家的最底层、最被人看不起的人。可悲哀的是,同样是在最底层,被人欺负,小伙计本应该同情孔乙己,他却说:只有孔乙己到店,才可以笑几声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我认为这句话是才让人寒心的,甚至比孔乙己的死,还要伤人心。一个弱者天天被人欺负,只能抽刀向更弱者,而且仿佛他这辈子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孔乙己之上,他记得孔乙己,只是因为孔乙己带给他的“快乐”,而且数年过去了——“至今仍然记得”——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。
后文中,又多次出现小伙计对孔乙己的鄙视,孔乙己想跟小伙计说两句话,问他:“茴香豆的茴字,怎样写的?”小伙计是怎么想的呢——讨饭一样的人,也配考我么?他是非常不耐烦的,根本不愿意搭理孔乙己,然后奴着嘴走了。
于是在咸亨酒店形成了一个明显鄙视链:
第一阶层是丁举人等有功名的读书人,鄙视他以下所有人;
第二阶层是掌柜,掌柜鄙视短衣帮、小伙计和孔乙己;
第三阶层是短衣帮,鄙视小伙计和孔乙己;
第四阶层为小伙计,鄙视孔乙己;
第五阶层为孔乙己,只能被所有人鄙视和嘲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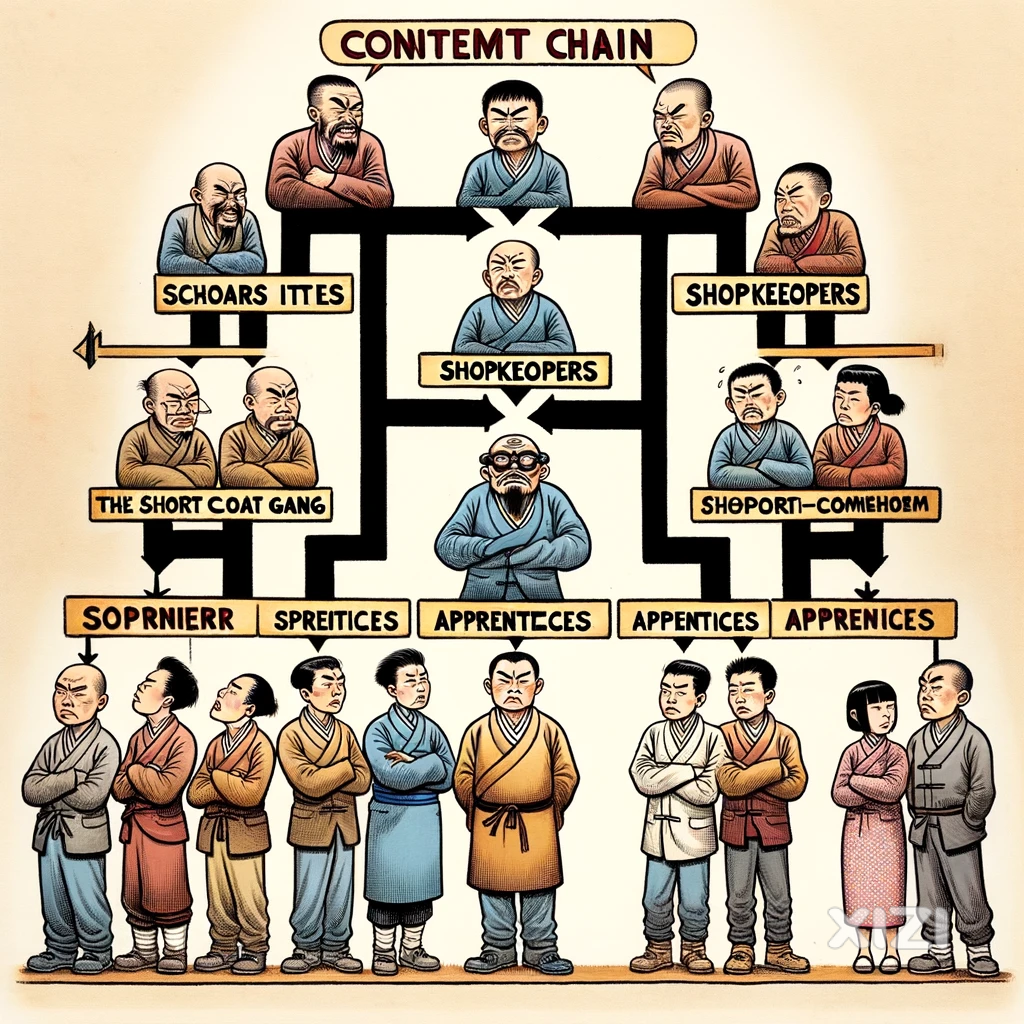 描述:咸亨酒馆阶级鄙视链(AI自动生成)
描述:咸亨酒馆阶级鄙视链(AI自动生成)
这个链条里面,上层人鄙视下层人、欺压下层人,下层人侍奉上层人,从不敢反抗上层人,尊卑有序,这就是咸亨酒店为中心的社会秩序。其实鲁迅是在前面部分的描写中将咸亨酒馆的隐形“等级”刻画出来。这种等级秩序是深入人心,深入骨髓的,而更多的,是统治阶层对百姓的灌输,鲁迅曾经在《灯下漫笔》中写道:
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,有贵贱,有大小,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,但也可以凌虐别人;自己被人吃,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,不能动弹,也不想动弹了。因为倘一动弹,虽或有利,然而也有弊。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——“天有十日,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,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,公臣大夫,大夫臣士,士臣阜,阜臣舆,舆臣隶,隶臣僚,僚臣仆,仆臣台。”(《左传》昭公七年)
但是“台”没有臣,不是太苦了么?无须担心的,有比他更卑的妻,更弱的子在。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,他日长大,升而为“台”,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,供他驱使了。如此连环,各得其所,有敢非议者,其罪名曰不安分!
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,每个人都在服从上等人,每个人又都在当欺负弱者的强者,咸亨酒馆的鄙视链也是根植于此,即便酒店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底层人,可这些底层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出来,掌柜自然要比短衣帮尊贵,毕竟自己是小老板;短衣帮自然要比小伙计尊贵,毕竟自己是客人;小伙计自然要比孔乙己尊贵,毕竟自己有正经的差事——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践踏之上。孔乙己就要成乞丐了,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,还要穿上破旧的长衫,以显得身份地位不同,不愿与下苦力的粗人为伍。时至今日,我们很难说消除了这种思想,比如有些大学生,四肢健全,难以找到工作,也不会去送外卖或者去工地干活,拿得钱少,也要在办公室里面,也要分出尊卑贵贱来,毕竟自己是大学生,怎么能干体力活呢?再比如我们听到“教授”这个词,就会产生尊崇感,只是基于“教授”这个身份,我们不了解他的知识文化,也不了解他的德行,就预设了他是“上等人”,更不用说企业单位里的“领导”了。我们也许思索一下,自己也是不是在鄙视链中呢,一面对所谓的上等人卑躬屈膝,一面对所谓的下等人嗤之以鼻。我们需要承认的是,有些人是会比其他人有钱、有权力、有文化,但都不是“恃强凌弱”的理由——平等的尊重和平等的关怀,才是社会文明的体现。读书学习是为了文明开化,如果只为了功名利禄,只是为了凌驾于他人之上,很难说,这不是一种野蛮的退步。当我们批判很多人思想的时候,并不说很多人是“有原罪”的,而是社会给他们传递了这种思想,是社会现状让他们不得不持有这种思想。
如今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如此,农民和工人就是这个社会最受鄙夷的人,这种鄙夷不仅仅是思想上的,也与待遇和社会福利相关,或者说,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于国家的种种都在“鄙夷”他们,无论退休金,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,这么多年以来,很多人都在说内卷,都在说高考问题以及种种弊端,在我眼里,这个世界的社会架构就是“等级”,人们争破头皮,就是为了获得这“人上人”的机会罢了,而高考(公务员考试)只是其中极少数的相对公平的通道。身为一个社会底层人,为了生活和尊严,没有办法,只能去“卷”。有意思的是,内卷到最后,以为终于做了所谓“人上人”,其实只是做了达官贵人的“奴才”,换句话说,奴才们越“卷”,主子们越开心。私以为,真正解决内卷,是社会分配,提高底层人的福利和待遇,让他们即便从事体力劳动,也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基本的社会尊严——至于怎么实现,我就不知道了。废话说得有点多,回到正题,鲁迅先生写《孔乙己》,并非为了嘲笑孔乙己,纯粹为了批判孔乙己,而是为了改良社会土壤,但改良社会土壤,又不得不从人的思想教育上开始。尽管孔乙己以读书人、上等人自居,宁可饿死,也不愿意下地干活,是食古不化的,可他又是矛盾而特殊的,他具有平等的尊重和平等的关怀,他是有反抗意识和觉醒者潜质的,为何这么说呢,我们下期再作详细解读。